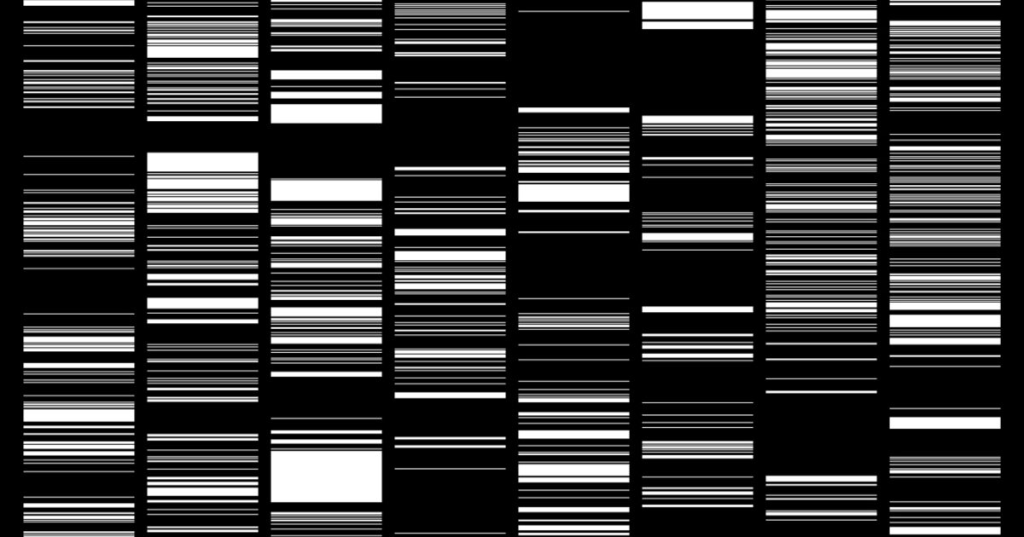
K.F. Frac, Cr.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是个数学意义上的密室。他每天在这个密室的一角坐下,工作或者不工作。
他感到意识在慢慢恢复。——不是在月亮或其他行星上,不是濒死士兵,只是刚睡醒。
眼睛,睁开。脖颈有未释放的压力,拧一拧枕头,再闭一会眼。
一天的开始一直都从右侧的光计起。
上午即将结束,除去中午这四边不靠的阶段可以暂做逃离想,下午有与 boss 的会面。他感到一阵湿重的压力。食物提供能量,咖啡(和燕麦奶)提供最便捷的逃离选项。虽然基本已经不起作用了,但在啜饮咖啡时你有借口说「请等一下,我喝完这杯咖啡就来」,使听者感到一种受咖啡背书的尊重。
他的思绪还有一些漫游的时间。不同于他的躯体,他的思绪很少愿意停留在同一处,甚至很少停留在线性路径上。他在思考的时候会同时遇到不同层级的阻碍,于是会同时感受到不同次元的挫折,进步则被分散出去,看起来实在可怜。他在期待有一天这些阻碍(就像他遇到它们时)会突然同时灰飞烟灭。湿重的压力在渗水。
他拿不定主意在日间分配多少精力。不过呢,分配多少精力自己的工作也没显现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他拿不准自己到底是哪里不对,还是哪里对了,还是压根就不该疑惑这个问题。
自己真的是人类的一部分吗?自己该为这个问题还是它的答案感到忧虑吗?为什么牵扯出一股谢罪的必要?我得向谁谢什么罪?
「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有疲劳的时候,比如现在。放过自己吧,他想,不必每个句子都要惊世骇俗完美无瑕。语不惊人也可以。他这么想,一边吃完了粥,喝了咖啡。穿了袜子,戴了帽子,出门,锁门,去另一个封闭空间度过几小时。
他的办公室没有窗户。看起来理所当然,有窗户的位置,但因为是在两楼夹缝之中,没有窗户存在的余地,所以就没有窗户。与其说是没有窗户,不如说是没有与外部空间直接连接的拓扑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是个数学意义上的密室。他每天在这个密室的一角坐下,工作或者不工作。
近日来他被抽象地要求去考虑未来的问题。坐在密室之中,未来显得非常含糊,而且可怕。他没来由地觉得自己害怕什么东西,但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反复向自己和愿意听他叨叨的人说他想知道那个他想知道的东西是什么。话是没错,但是没人听懂。他自己也不懂。——所以才要问啊,元问题也是问题,元疑惑也是疑惑。但是目前还只有一条时间线,元问题占据了之后,实在域的任务就不想去理会了。他也感到难受,但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似乎不是一种合法合规的忧虑。尽管他已经把他的治疗师吓了个半死,他仍然觉得不知怎么传达。他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痛苦,尽管治疗师已经激动到戳镜头。
我很痛苦,但我有这个资格自称痛苦吗?
他可以忍受流血,也可以忍受疼痛,甚至也可以习惯流血加疼痛;他所不能习惯的是上述情形带来的恶心。恶心,表示身体有什么东西在排斥另一种什么东西;但是两样他都不知道是什么。他不喜欢这种黑箱式的痛苦。不过即使如此,痛苦也是必要的。痛苦是边界提示,知道这一点就可以。
有时他会盯着自己皮肤上由于种种因素形成的痕迹。比如珠宝的压痕,汗水的气味轮廓,被服衣裤留下的温度梯度。偶尔会出现一些神秘的划痕,会稍微出点血,疼痛一下。这让他奇异地确认到自己仍是活着的生物,活着的动物。
比起无神论来,他在情感上其实更接近泛灵论;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相信」泛灵论的,他更像是会愿意受泛灵论的感动,然而理性上并不做判断。他的理性已经非常疲劳,不大会主动介入情感。这也是一种他不知如何向旁人解释的机制。他在真诚而苦心地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天才,哪里可以称之为天才;因为不如此的话,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疑惑如此难以解释。
他每天会等待时间进行到一定时刻,之后去吃当日的正餐,餐毕一般就回到他方方正正的卧室中去。在办公室度过的时间不能说是毫无记忆,但是要记得也着实需要花费一番力气。一般离开办公室时他基本已经进入关机状态。最近他很容易倾向于用机器术语观察自己,可能有点过头了。
他像喜鹊一样喜欢亮闪闪的东西,有一阵手上身上头上戴满了饰物。又过了一阵,嫌累,又一个个摘下来,只留下当下最得宠的一二件。这些美丽能让他确认一部分美丽属于自己;穿戴在自己身上多少也是自己的一部分了。就好像衣服是皮囊的一部分一样。
皮囊是好东西,极好的。它是你活着的唯一倚赖,至少在意识能上传之前没有代替物。一般提到死亡,也都是指皮囊之消灭。这具皮囊有喜怒哀乐,咸甜苦辣,血肉骨头等等,应当是珍贵的仅此一家的宝物。称之为「臭皮囊」,对死亡和生命都失之公允。
死亡是我的朋友,他放松下来想道。是的,它是我忠诚的朋友。当它来访,我将欣然与之同行。在那之前,我不必为此忧惧。
船过水无痕,那又怎么样?
今晚吃咖哩饭吧。他感到血在皮肤之下(在有裂口的地方,之上)流动,肌肉彼此联结,骨骼演示精妙的动力学。我活着,挺不错。
死的象征其实是友善而慈悲的。在学习直面他自己时(困难得无以复加),托尔斯泰以一种简单天真而淳朴的姿态出现在视野中。他练习直面他自己卑劣的部分,居然从中获得直面他最华美的部分的力量。这是何等诡异。
诚挚地写下不那么奇崛的句子,似乎也不再是个需要抗拒的事情(还需要练习),不过错别字仍然是受轻蔑的。他带着如今已经归入正统的傲慢和狂气,笨拙地练习普通的语言。
留下评论